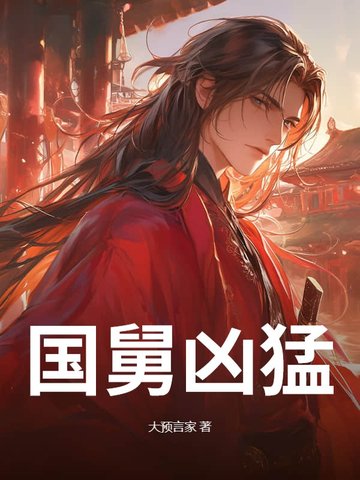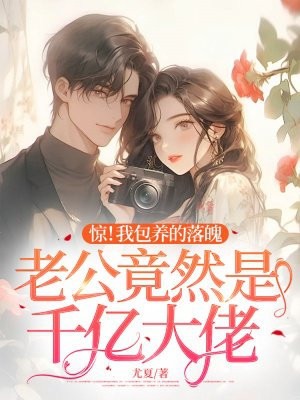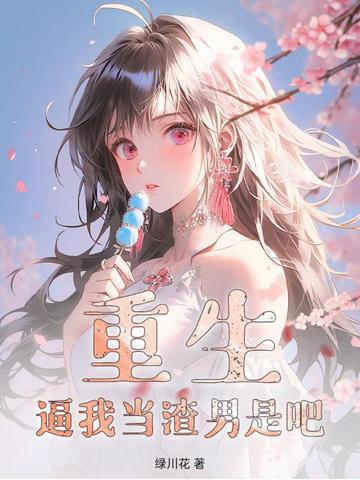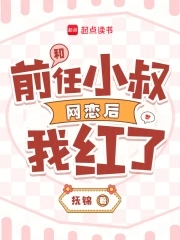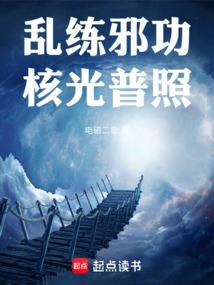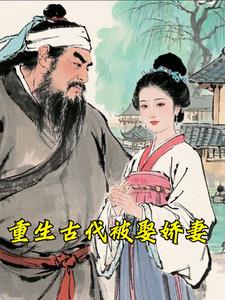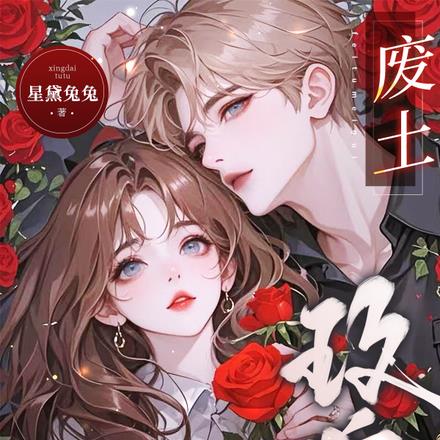第一百零三章 幸好中国文坛有胡为民在(4/5)
孩子上课。
当其他小说描写红兵撕书时,这篇小说却在写乡村教师是如何传承知识的。
正如扎西多(查剑英)在文艺报上写的批评文章所说:“《孩子王》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可能——不是‘我们被毁掉了什么’,而是‘我们拼命保住了什么’。”
书店里,梁晓生突然摘下眼镜擦了擦。
在书店的这半个多小时,他收获颇丰,他的心中也有了答案,似乎到了离开的时候。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发现有位读者要求购买《孩子王》的单行本:“同志,我就要这一篇的有吗?”
问到原因,这个戴眼镜的中年人笑了笑:“我想寄给我的朋友,他也是乡村教师。”
众人闻言,不由肃然起敬。
梁晓生回到北影厂宿舍,他已经知道自己该创作什么样的作品了。
“知青文学,这才是真正适合我的题材!”
他想起在北大荒时,听老战友说过一个故事。
那个故事的背景是在上山下乡开始的时候,某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副指导员一个来自南方大城市的小姑娘,在连队连年歉收的情况下,仍未动摇屯垦戍边的信念。
她立下军令状,率领先遣小队向未开垦的“满盖荒原”进军,率领十几个开垦者与狼群搏斗,与雪暴斗争,终于战胜了“鬼沼”。
当第一场春雨降临到她们开垦的乌油油的沃土时,副指导员却和两名与她同样年纪的同伴不幸牺牲,长眠在那片沃土。
越思考,梁晓生越觉得这个故事特别适合自己。
当时,广大知识青年是怀着无比崇高与神圣的心情,饱含创业的激情与建功立业的英雄壮志由城市来到农村。
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把满腔的热血和赤诚都奉献给了“插队”的那片热土,有的知青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如果像伤痕文学,直接否定了上山下乡,那对于他们这些用青春和热血书写的岁月,他们近乎痴守的基本信念,岂不是要受到根本性的否定和动摇。
这些,梁晓生曾经没有仔细思考过。
毕竟《伤痕》和《班主任》发表时,他也看得热泪盈眶。
等到这类作品越来
本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