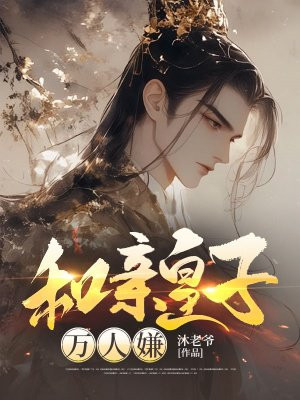第23章外面3(3/5)
可以把过道当餐厅;可以在两栋楼之间的狭缝处搭建居所,而且还能遗传后世;居住空间已经是捉襟见肘了,至于其他功能的需要,便只能开发跟创造了,比如晾晒些日常衣物之类的,他们除了房顶上几乎再就没有什么条件能提供给他们晾晒空间了,不过没关系,即使家在主干道旁他们也能想出办法来,仅用一根竹竿便可轻松解决了,那竹竿一头往往是搭在街道边的树枝上的,而另一端可以搭在自家的窗台上,这一景观,由来已久,而且已经被视为上海智慧,并且已经作为一种特色文化世世代代地流传下来,所以并不必担心有城管之类的管理部门来给他们冠上个影响市容之类的罪名而遭受阻止。
燥、傲、乱、挤!这是伍哲眼中的上海。他觉得能够在这里生存下去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要么更骄傲,清高到蔑视一切;要么就是更谦虚,低微到看路边的垃圾都觉得它是神圣的。
这是一个彻底摒弃了自然环境的地方,这就让本来就不大丰厚的自然文化也所剩无几了,伍哲感到,上海似乎是一个从物质跟精神两方面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地方。
然而这里毕竟是超级大都市,民众是有见识的,再传统保守的老妪,也会知道一些在上海举办的国际会议的日程,几乎不必培养,这里的民众就很有国际范的秩序感跟优越感。只是本地人很以本地户口为傲,大都看不起外来人,“阿拉桑嘿宁呀!”这是一句表明籍贯的上海话,是每个上海人面对外来人都必备的台词。他们似乎特别看不起东北来的人,可怜的上海人出于怕和难以沟通两种障碍令他们排斥着北方人,觉得他们粗野、蛮横,不可理喻,其实在北方人眼里上海人也挺蛮横的。两者相较只不过是方式不同而已,北方人用情绪和拳头,上海人用语言:“你不可以这样子的啦好伐?!”,彼此各异的处世方式令这种相处产生了恶性循环,而且大有世代相传的危险。
给伍哲的感觉,在这里,他看不到一个真正闲适的面孔,每个人都是忙碌的,紧张的,他们的生活状态很像是一群蚂蚁,而且是工蚁。除了生存所需便是工作,精神层面的追求和享受仅限于看上去怎么样才会做,内心的真实想望和追求不是难以实现,而是根本就没有了。就连广场上散步遛弯的老者也看不出悠闲惬意的神情来,到很像是只是为了这个场所
本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