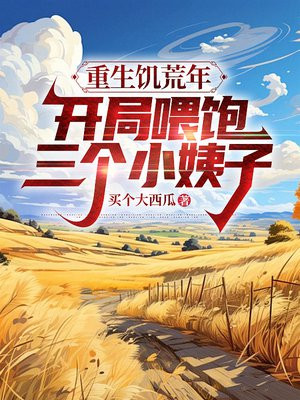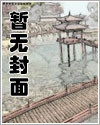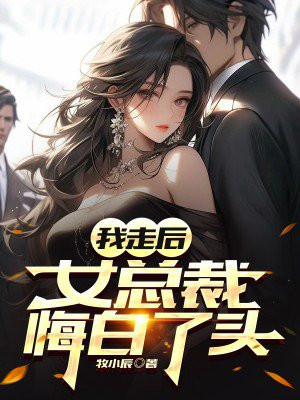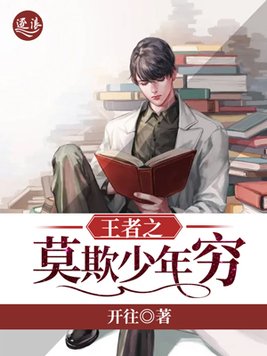第56章 太学清谈:算学解经惊四座(2/4)
浅。
渐渐地,话题转到了《尚书·禹贡》一篇。
一位老儒正在讲解九州的地理划分和贡赋制度,引述着汉代经学大师们的注疏,阐述着其中蕴含的王道思想和地理观念。
众人皆点头称是,气氛一派祥和。然而,在仔细聆听并结合我脑中那点可怜的地理知识和基本的经济学常识进行思考后,一个疑问却悄然在我心中升起。
按照老儒所引述的传统注疏,《禹贡》中记载的某些偏远地区的贡赋数量和种类,似乎与其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以及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存在着一些难以解释的矛盾。
比如,某个极西之地,需要向数千里之外的京畿缴纳大量的、不易运输的丝帛或漆器,这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成本之高昂、损耗之巨大,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犹豫了片刻。我知道,质疑经学大师的注疏,尤其是在这种场合,是非常冒险的行为,很容易被视为狂悖无知,甚至引来群起而攻之。
但……我心中那份对逻辑和事实的追求,以及一丝想要展现自己独特思维的冲动,最终还是战胜了胆怯。
在老儒讲解告一段落,众人品茶沉吟的间隙,我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恭敬地行了一礼,然后小心翼翼地开口道:“晚生斗胆,请教老先生一事。”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到了我这个不起眼的末席年轻人身上,带着惊讶和审视。老儒也微微抬眼,示意我说下去。
“方才听老先生讲解《禹贡》贡赋制度,晚生深为叹服。”
我先是恭维了一句,然后话锋一转,“然晚生心中有一疑虑,不知当讲不当讲。《禹贡》所载,如梁州之贡‘厥贡漆丝’,雍州之贡‘厥贡惟球琳琅玕’,此二州距京畿路途遥远,山川阻隔。
若按注疏所言,每年需输送如此数量之丝帛、美玉,其运输之艰难,耗费之巨大,损耗之惊人,恐非当时人力物力所能承担。
晚生愚钝,窃以为,其中或有晚辈未能理解之处,恳请老先生解惑。”
我的问题一出,现场的气氛顿时微微一凝。
一些人皱起了眉头,显然觉得我这个问题有些不合时宜,甚至是在挑战权威。
那位老儒也捋着胡须,沉吟不语
本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