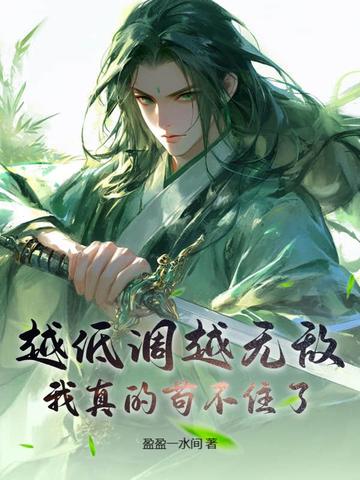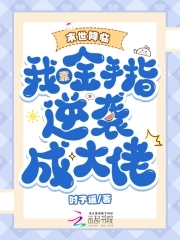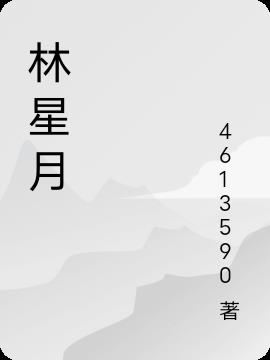斗笠下的困重影(7/19)
在紫缎上。叶承天凑近时,闻到那处皮肤带着淡淡的酸腐气,混着汗渍与茶菁的涩,正是脾湿不化、气血瘀滞的征兆。
“焦三仙得炒出‘天地人’三才之焦。”他转身掀开竹制药筛,三团金黄的粉末静静躺着——焦麦芽蜷曲如钩,表面挂着细密的焦斑,像晒透的稻穗;焦山楂碎瓣边缘微卷,红中透褐,保留着果肉的肌理;焦神曲块上布满蜂窝状细孔,散发着炒谷芽的焦香,正是去年霜降后用灶心土炒至“存性”的上品。研钵捣药时,木杵撞击声混着艾条引燃的“噼啪”响,金黄的粉末在阳光里扬起,落在紫痕周围的皮肤上,倒像是给瘀伤镀了层暖春的阳光。
茯苓汁是早上煎药时特意滤出的头道汤,乳白中泛着松脂的淡金,调入药粉时发出“沙沙”的细响,凝成的膏体带着颗粒感,却在触到皮肤的刹那化作温软的泥——焦麦芽的纤维轻擦着瘀肿处,焦山楂的果酸带来细微的刺痒,焦神曲的谷香混着茯苓的清润,像有人用晒暖的粗麻布,轻轻揉按久浸冷水的肌腱。“这焦香能醒脾开胃,”叶承天指尖在药泥上点出几个凹窝,“就像您炒茶时,锅气到了,青气才会散,香气才能聚。”
艾条是医馆后园自种的蕲艾,端午采收后在北屋檐阴干三年,此刻燃在青瓷灸盏里,腾起的烟雾呈淡金色,艾绒的苦味里裹着草木灰的沉郁。当艾条悬在足三里穴上方半寸时,采茶女忽然绷紧的脊背慢慢松下来——温热的气浪像春日里煨茶的泥炉,隔着粗布衫仍能感到穴位处的皮肤在轻轻发烫,仿佛有团小火苗在脾胃深处的湿土里钻洞,把沉积的寒湿一点点烘成水汽。
“您看这足三里,”叶承天用艾条尾端轻点她膝盖下的凹陷,“胃经的合穴,好比炒茶锅的炉心,火候足了,锅里的茶才经得起翻炒。”他说话时,药泥里的焦三仙颗粒正被体温慢慢软化,紫痕边缘的青肿处渗出淡红的血色,像冻僵的土地开始回暖。采茶女盯着艾条上跳动的火星,忽然想起去年清明前炒茶,火候不够的那锅茶总带着青涩,正如她这被湿寒困住的脾胃,原来也需要这样恰到好处的“火候”来唤醒。
医馆的药柜传来阿林整理药材的响动,陶瓮里的陈皮香混着艾烟飘向窗外,远处茶园的竹篓碰撞声比来时清脆许多。叶承天换艾条时,指尖掠过她腰间的草绳——那用野山藤编
本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