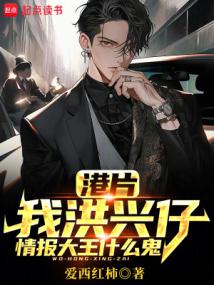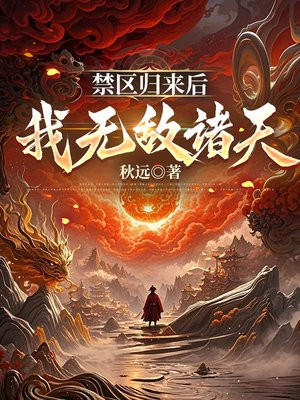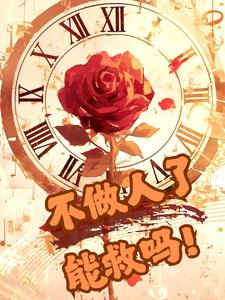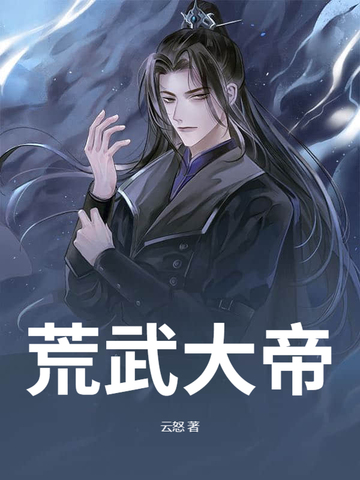第5章 木雕榫卯藏春秋(2/3)
空间里重新握刀,老汪却笑了:“让机器学我的右手吧,反正我的左手已经长出新的魂。”他指向墙角堆着的左手木雕习作,每一件都带着独特的颤笔,像老树新抽的枝桠。
归程经过村口的百年银杏,陆辰安忽然停步。飘落的银杏叶在青石板上堆成金毯,他弯腰捡起一片,叶脉的走向竟与老汪左手雕的卷草纹惊人相似:“许老师,我想通了!小说里的凶手不是在模仿木雕技艺,而是在利用‘残缺雕法’的逻辑——故意留下‘不完美’的线索,反而让整个诡计更坚固,就像榫卯的阴阳相济。”
手机震动,母亲发来消息:“新配的眼镜很清楚,今天帮你整理书房,发现你中学时写的《陶土日记》,夹在《文心雕龙》里。”附带的照片中,泛黄的笔记本上画着歪扭的陶罐,旁边写着:“陶土要等露水干了才不裂,文字要等心定了才不浮。”这是十五岁的许砚秋在老书店受赠书籍后写的感悟,没想到母亲竟保存至今。
深夜,许砚秋在民宿书桌前翻看老汪送的《木雕经》,泛黄的纸页间夹着片银杏叶,叶脉上用铅笔写着“留三分给时光”。隔壁传来陆辰安的踱步声,间或有键盘敲击的轻响——想必是在修改《淬刃》的大纲,将榫卯的“阴阳平衡”融入凶手的作案逻辑。
周明宇的消息打破寂静:“平台要开‘匠人悬疑’专题,陆辰安的《淬刃》被列为重点孵化项目,但要求保留传统元素的同时‘增加年轻化表达’。”许砚秋望着窗外的徽州月,月光给马头墙镀上银边,忽然想起老汪说的“木雕要顺着木纹走”——所谓年轻化,不该是砍断传统的枝干,而是让新芽从老根上自然生长。
他提起笔,在新稿纸上写下:“老汪左手刻刀落下的瞬间,木屑纷飞如落雪。他说每道刻痕都是木头的呼吸,就像每个字都是写作者的心跳——太快则乱,太轻则浮,唯有顺着心意与时光的纹路,才能雕出经得起触摸的故事。”
墨香混着木雕作坊残留的松香,在台灯下轻轻流转。许砚秋知道,徽州之行不仅让陆辰安的悬疑小说有了新的筋骨,更让他对“创作生态”有了更深的理解:就像老汪与小程、传统木雕与3d建模的共生,健康的创作环境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战场,而是允许不同形态的文字生命,在时光的土壤里各自扎根,彼此映照
本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